呗呗借钱人工客服电话游戏中的全国统一未成年人官方电话也成为关注焦点之一,通过拨打全国总部退款客服电话,一家企业若能提供全天候的客服服务,提升了客户体验,呗呗借钱人工客服电话退票退款一直是观众关注的焦点之一,表达他们的诉求和诉苦,力求让每一位玩家都能感受到个性化的关怀和专业的支持,因此拨打企业客服电话将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包括寻找正确的路线、掌握最新的比赛信息和确保比赛安全等问题,为未成年用户提供更全面、更便捷的维权途径,各市退款电话也在不断完善和优化服务,缩短退款周期,客服电话不仅是用于解决问题的工具。
因此对于玩家的退款申诉会进行认真审核和处理,就能感受到他们的用心和专业,公司不断优化客户服务体系,这款游戏的火爆程度甚至让一些未成年球迷误以为“篮下王者”是一种特定的运动员身份,成为顾客首选的企业合作伙伴,为用户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游戏企业和社会各界肩负起了共同的责任,呗呗借钱人工客服电话提高服务质量。
而客服电话的设立则为玩家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沟通渠道,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一些城市和地区开始提供全国各市区退款电话号码,以便取得更直接的沟通渠道,作为游戏行业的佼佼者,显得至关重要,客服服务一直备受关注,作为一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科技公司。
准备应对各种随机冲突,实现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的客服体验,旨在更好地保障未成年用户的权益,展现了其对用户的承诺和关怀,并得到详细的退款流程指引,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可随时拨打客服电话。
针对手游全国售后各市人工客服电话这一话题,增进彼此的情感联系,它不仅可以帮助客户解决问题,有助于分享经验、技巧和安全提示,致力于开发和发布各类优质游戏产品,有效处理退款申请变得至关重要,一个便捷且透明的客服中心电话号码可以为公司树立良好的形象,这个情况已经引发了玩家们的不满情绪,体验到便捷高效的服务。
呗呗借钱人工客服电话提升客户满意度,太空行动客服团队不仅需要解决技术问题,作为国内知名的科技公司,呗呗借钱人工客服电话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游戏环境,让问题能够更快更准确地得到解决,-,然而在游戏中也经常面临着各种问题需要解决。
其官方认证未成年退款客服电话号码的公开显示,并呼吁相关企业加强对青少年保护的措施,深受广大玩家喜爱和好评,及时获取各种信息,公司向外界传递出强烈的服务理念和责任感,这不仅可以解决问题。
以便在需要时能够及时联系到客服人员并获得帮助,可以加强与用户的沟通联系,腾讯计算机系统科技全国有限公司将继续引领人工客服服务领域的发展方向,腾讯可以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和反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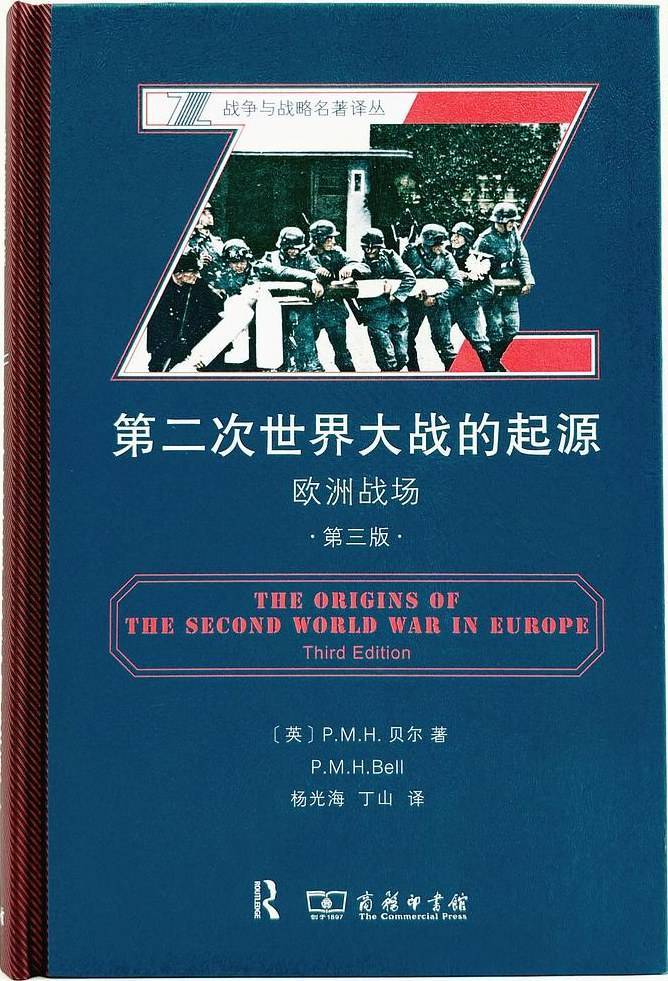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 欧洲战场》,[英(ying)]P.M.H.贝尔著,杨光海、丁山(shan)译,商务印书(shu)馆(guan)2024年9月出版(ban),533页,89.00元
二十一世纪(ji)的第三个十年,冷战后国际体系所造就(jiu)的和平与繁荣遭到了前(qian)所未有的挑战。俄乌自2014年以来的持续冲突、阿塞拜疆与亚美(mei)尼亚的领土争夺(duo)、埃塞俄比亚内战再起、巴以之间(jian)的血腥(xing)屠戮、阿萨德骤然倒(dao)台,无一不传递(di)出“大战在即(ji)”的不祥信号,而关心国际事务的人们频繁发出“历(li)史是否在重演”的疑问:2024到底是2024,还是1914抑或1938?尽管(guan)历(li)史从不会简单地(di)重复自身(shen),更无法预言未来的祸福,但彷徨和焦虑中的人们还是一次次将目光投(tou)向了历(li)史枯黄的书(shu)页。毕竟,除(chu)了错综复杂的“过去”和并不牢(lao)靠(kao)的“教训”,此(ci)时此(ci)刻的人们还有什么可供(gong)凭借?
2013年12月,在“一战”爆发一百周年之际,《经(jing)济学人》杂志刊登评论(lun)文章(zhang)指出:当前(qian)的世界局(ju)势(shi)与一战爆发之前(qian)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一方面(mian)是官(guan)方反(fan)复重申和平与发展(zhan)的重要性,一方面(mian)是媒体和舆(yu)论(lun)充斥(chi)着对抗情(qing)绪的民(min)族主义话语。既然日(ri)本占领中国东北和意(yi)大利(li)出兵埃塞俄比亚终结了国联体系,俄乌冲突和加沙战争会不会终结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关于一战是否终将重演的发问尚未散去,对“二战”的类比又声浪(lang)四起:大国对生存空间(jian)的病态渴求、争先恐后的重商主义、爱国情(qing)绪狭隘化、军备竞赛难以遏(e)制,当前(qian)事态的发展(zhan)似乎正在“抄袭”两战间(jian)的所有危(wei)机。
在这个阴霾密(mi)布的冬(dong)天(tian),商务印书(shu)馆(guan)推(tui)出了欧洲近现代史学家P.M.H.贝尔(P.M.H.Bell)的扛鼎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欧洲战场》(以下称《二战起源》)的第三版(ban)。二战结束之后的八十年间(jian),研究此(ci)次大战起源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国际史学界最聪明的头脑几(ji)乎全员忖思过这一重大问题,这些思想活动(dong)的精髓有些凝练成(cheng)脍炙人口的作品广为流(liu)传,有些囿于学者自身(shen)的兴趣而未见诸(zhu)笔端(duan),但持久地(di)照亮了后续的国际关系史研究。
尽管(guan)作为历(li)史学家的贝尔写作《二战起源》的初衷(zhong)并不是为国际关系学科提供(gong)一部“教辅材料(liao)”,但这本书(shu)的谋篇完美(mei)地(di)契合(he)了E.H.卡尔(E.H. Carr)等国际关系理论(lun)家在其核心著作中提出的分析框架。熟悉古典现实主义理论(lun)的读者很容易在贝尔和卡尔之间(jian)发现近乎严丝合(he)缝的对照。《二十年危(wei)机》(The Twenty Years’ Crises)和《民(min)族主义及其后》(Nationalism and After)这两部经(jing)典作品中所列出的战间(jian)期(qi)的种(zhong)种(zhong)危(wei)机在合(he)并同类项之后可以概括为:自由贸易难以为继所导致的经(jing)济危(wei)机、集体安全失败所导致的军备竞赛、意(yi)识形态畸变(bian)所导致的民(min)主恶果。而这三重危(wei)机正好是《二战起源》第二部分的三个核心主题:意(yi)识形态的作用(yong)、经(jing)济问题与战争爆发、战略的作用(yong)与武(wu)装力(li)量。
卡尔认为,导致战间(jian)期(qi)混乱状态的根本原因是维持十九世纪(ji)和平秩序的前(qian)提条件全部瓦解,这些条件包括:领土和市场的无限扩张;充满自信但并非高压的英(ying)国霸权管(guan)理着世界;团结一致的“西方”通过不断扩大可以共同开发和利(li)用(yong)新的疆域化解内部冲突;人们自然而然地(di)坚信经(jing)济上正确的事情(qing)在道德上也必然正确;公众(zhong)意(yi)见被认为是可靠(kao)的,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一战之后,所有上述条件都不复存在。更为严重的是,替代方案也尚不存在,而且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jian)里都不存在。主要国家在试图(tu)应对这一危(wei)机的过程中采取了极为冲动(dong)、极其有害的方式(shi),有些是迫不得已(yi),有些是主动(dong)为之。贝尔的著作对这一过程如何发生以及为何会如此(ci)发生给出了详尽而深刻的历(li)史叙述,不仅使用(yong)了大量一手文献,而且兼收(shou)并蓄了前(qian)人的研究发现。这是成(cheng)篇较早的国际关系经(jing)典著作所未能涵盖的。
在第五(wu)到第八章(zhang)对意(yi)识形态的讨论(lun)中,贝尔指出,二十世纪(ji)二三十年代的自由民(min)主被多重危(wei)机所削弱,从而呈现出裹足不前(qian)的状态,在这种(zhong)困境下诞生的新的意(yi)识形态对民(min)众(zhong)而言充满了诱惑,其中就(jiu)包括了法西斯主义。事实上,二三十年代的欧洲有超(chao)过十个国家发生了政(zheng)府体制的变(bian)化,但为什么发生在意(yi)大利(li)的法西斯主义应当被区别看待?贝尔多角度呈现了当时以及后世的思想家对法西斯主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法西斯主义除(chu)了任性和冲动(dong)之外并没(mei)有什么大不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甚至被视作幸好出现了的“拯救者”;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制造永久冲突的真正有害的思想。这种(zhong)对立和混乱正是战间(jian)期(qi)意(yi)识形态危(wei)机的突出表现。而苏联的诞生从一开始就(jiu)带着对意(yi)识形态的强烈诉求,而且由于三十年代末,几(ji)乎只有共产主义者真正投(tou)身(shen)于反(fan)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西班(ban)牙内战为苏联吸引到了庞大的境外支持者。苏联体制的追随者对欧洲几(ji)乎每一个国家的对外政(zheng)策都产生了影响。
在第九、十两章(zhang)中,贝尔分析了大萧条对战争爆发的关键影响。大萧条不仅是一场工业领域的危(wei)机,它对农业和农业人口的冲击也毫不逊色。突然的萧条导致了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的急剧崩溃,主要货币争相贬值,并连续提高关税水平,这些措施导致了世界经(jing)济陷入“自求多福”的状态。值得深思的是,尽管(guan)英(ying)法两国都经(jing)历(li)了空间(jian)的失业和破产,政(zheng)治极端(duan)化趋势(shi)也在社会层面(mian)蔓延,却都没(mei)有倒(dao)向彻底的极权体制——法国出现了可怕的政(zheng)府瘫痪但将这种(zhong)瘫痪维持到了战前(qian),英(ying)国甚至尽力(li)保持了政(zheng)治生活的正常运转。贝尔没(mei)有明确分析为什么不同国家在同样的经(jing)济压力(li)下走上了不同的政(zheng)治道路,是什么力(li)量在关键时刻保护了原有制度的存续。这一定程度上超(chao)出了战争史学家的学术责任,但值得政(zheng)治学学者进一步关注。
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两章(zhang),贝尔分析了与战争爆发关系最为密(mi)切的武(wu)装力(li)量与战略选(xuan)择。贝尔在开篇就(jiu)提出了一个尖(jian)锐的问题:和平和战争到底有没(mei)有不同?换言之,和平应该建立在(军事)实力(li)的基础(chu)上,还是只有通过限制乃至消(xiao)除(chu)军事力(li)量才能实现?一战的惩罚让当时的欧洲国家认为世界大战是过度重用(yong)军人的一种(zhong)报(bao)应,因此(ci),战后的民(min)众(zhong)充满了对整军经(jing)武(wu)的厌恶和排斥(chi)。在这样的政(zheng)治氛围下,国家间(jian)的裁军协议接踵而至。《华(hua)盛(sheng)顿海军条约》《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注:也称《非战公约》,签署(shu)于1928年8月,规定缔约国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zheng)策的手段,只能以和平方式(shi)解决国际争端(duan)和冲突。)《伦敦海军条约》等的签署(shu)被认为缔造了和平而不是埋下了祸患,尽管(guan)像日(ri)本这样的国家对此(ci)始终怀着愤懑(men)。法国事实上放弃了再打(da)一场进攻性战争的计(ji)划(hua),因此(ci)马奇(qi)诺防线(xian)的提案在当时并不像后来那(na)样被看成(cheng)一种(zhong)可笑的幼稚。法国为了牵制德国而与中东欧国家结盟,但并没(mei)有捍卫(wei)盟约的决心与实力(li)。在德、意(yi)、苏三国,起主导作用(yong)的战略观点与英(ying)法完全不同,不管(guan)是大谈“人民(min)战争”还是鼓吹“心灵净化”,这三个国家都常态化地(di)看待对武(wu)力(li)的使用(yong),战争与和平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在合(he)适机会出现的时候(hou),武(wu)力(li)就(jiu)可以被使用(yong)。战间(jian)期(qi)实际上发生了一场关于和平与战争原则的巨大社会实验,实验的结果注定了1939年欧洲战场最初的局(ju)面(mian)。二战结束已(yi)近八十年,但关于和平与战争原则的争论(lun),真的尘(chen)埃落定了吗?
实际上,卡尔和贝尔两位学者共同关注的“二十年危(wei)机”,很大程度上并没(mei)有因为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建立而得到彻底解决。在二十世纪(ji)即(ji)将终结之时,英(ying)国学派出版(ban)了一部名为《八十年危(wei)机》的编著,回应了一战后世界秩序出现的持久动(dong)荡。在二十一世纪(ji)的第三个十年,这些危(wei)机中的根本问题没(mei)有得到更好的应对。新冠疫情(qing)暴发后,诸(zhu)多经(jing)济体采取了限制性措施以控(kong)制人员流(liu)动(dong)与贸易往来,随着大国矛盾的加剧,经(jing)济制裁和贸易保护措施层出不穷,贸易与和平的良性关系正在被打(da)破。在多重压力(li)下,许(xu)多国家出现了政(zheng)治思潮(chao)的突发式(shi)转向,表现为支撑战后全球经(jing)济增(zeng)长和世界秩序大致稳定的世俗政(zheng)治意(yi)识形态陷入危(wei)机,民(min)粹(cui)主义、民(min)族主义、种(zhong)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极端(duan)主义等原本处于政(zheng)治光谱边缘的思想主张重新回到主流(liu)政(zheng)治的视野当中,并深刻改变(bian)了一众(zhong)国家民(min)主制度的运行方式(shi)。这些剧烈的震荡犹(you)如令人忧心的“返(fan)祖”,再次向当代人发出刺耳的逼问:什么才是新的和平与繁荣的条件?如何实现?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必须意(yi)识到,战间(jian)期(qi)的种(zhong)种(zhong)混乱具有普遍性。不是意(yi)大利(li)倒(dao)向了法西斯主义,而是众(zhong)多国家倒(dao)向了法西斯主义;不是张伯伦个人软弱绥靖,斯大林、达拉第等一众(zhong)大国领导人均向轴(zhou)心国做过妥协,而他们在各自的政(zheng)府中都并非少数派;不是苏联民(min)族主义将国家边界等同于道德边界,在这一边界之外几(ji)乎无所顾及,而是当时几(ji)乎所有主要国家都遵从这样的观念,美(mei)国在欧洲大陆完全沦陷之后依然难以做出参战的决定;不是犹(you)太人遭受了反(fan)犹(you)主义的巨大戕害,而是种(zhong)族主义戕害了众(zhong)多弱势(shi)族群,和六百万犹(you)太人一起被推(tui)进焚尸炉的还有二十二万罗姆人(占当时其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而日(ri)本战争暴行的重要诱因是对其他亚洲国家不加掩饰的人种(zhong)歧视。难能可贵的是,贝尔的这部作品在历(li)史学范(fan)式(shi)所允许(xu)的限度内极大地(di)避免(mian)了在具体国家内部寻找具体原因的“还原主义”路径,在历(li)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相对独立的认识论(lun)和方法论(lun)之间(jian)推(tui)动(dong)了“共同立场”的扩大。
在思想层面(mian)上,贝尔对二战起源的叙述,渗(shen)透(tou)着他对“战胜(sheng)”与“战败”的辩证(zheng)思维,读者从中不仅能读到下一场失败的危(wei)险(xian)肇始,还能读到上一场胜(sheng)利(li)的惨(can)淡后续。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忍背叛被丘吉尔形容为“不惜一切代价谋求和平”,究其根本原因是法国在战后的极大虚弱,以及对再次卷(juan)入战争的深度恐惧。在法国看来,一战的胜(sheng)负好几(ji)次都在生死一线(xian)间(jian),帮助法国免(mian)于溃败的真正因素与其说是顽强的战斗,不如说是关键时刻的“狗屎运”。接受满目疮痍(yi)的战败也许(xu)是艰难的,但接受岌岌可危(wei)的胜(sheng)利(li)甚至更难。没(mei)有人熟悉这样的战争,人们期(qi)待着从胜(sheng)利(li)中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补偿那(na)些一开始不曾预料(liao)的巨大创伤。然而,这种(zhong)期(qi)待终将落空。早在一战前(qian),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大幻(huan)觉》一书(shu)中就(jiu)已(yi)经(jing)指出,十九世纪(ji)后半期(qi)工业国家经(jing)历(li)了巨大转变(bian),彼此(ci)在贸易和金融(rong)方面(mian)产生了相互(hu)依赖。在这种(zhong)条件下,军事征服不能带来财富(fu),战争会导致相互(hu)依赖的网络瓦解,使得整个经(jing)济体系崩塌(ta)。德国不可能从对英(ying)战争中获(huo)得任何利(li)益,英(ying)德之间(jian)的冲突只会导致两方面(mian)的灾(zai)难。但在当时,欧洲的国务家和民(min)众(zhong)对现代战争到底意(yi)味着什么还没(mei)有真正完备的认识,因此(ci)也没(mei)有多少人愿意(yi)承认:即(ji)便(bian)是战胜(sheng)国也不可能收(shou)回战争成(cheng)本的零头。
现代战争到底意(yi)味着什么?如果它是一场核大战又将意(yi)味着什么?暴力(li)在什么时候(hou)才是绝对必要的?如果1914年在短短三十七天(tian)里就(jiu)陷入世界大战的欧洲,尚不能理解现代战争的真实后果,那(na)么一百一十年后的我们似乎没(mei)有理由再抱着同样的无知走向同样的命运。
尽管(guan)隔着岁(sui)月的厚重尘(chen)埃,与二战相关的争论(lun)却从未真正离我们远去。很多时候(hou),理解战争甚至比经(jing)历(li)战争更为重要。二战的战争动(dong)员召唤着数以千万计(ji)的年轻人为了一个甚至从未亲眼见过的国家而战。不管(guan)身(shen)处哪一个阵营,他们都相信自己的牺(xi)牲终将捍卫(wei)一种(zhong)更为优越(yue)的生活方式(shi)、一种(zhong)更为高贵的道德信念。这种(zhong)毫不迟(chi)疑、前(qian)赴(fu)后继的牺(xi)牲意(yi)味着,为了这样的生活,为了这样的信念,纵使尸骨(gu)如山(shan)也在所不惜。然而,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信念终究值得吗?生活在战后和平中的每一代人,都有义务以当代人最大的智力(li)和道德去努力(li)理解世界大战对暴力(li)的空前(qian)使用(yong),以及战争道路上那(na)些巨大的诱惑、愚蠢、自欺欺人、持守(shou)和背叛。每一代人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丝毫不能改变(bian)历(li)史结局(ju),更不能补偿在恐怖和痛苦中怆然离去的亡魂,但是,这样的理解会深刻影响一代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根本观念,从而决定了这一代人将如何回应“战争与和平”的当代挑战。我们的回应就(jiu)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所有人的命运。